编者按:最近,曾广泛流行的口袋书、文库本又再次翻红。资深出版人赵强认为,这种图书类型契合当下的快节奏生活,是出版机构对变幻莫测的图书市场精准研判之后的“重拳”出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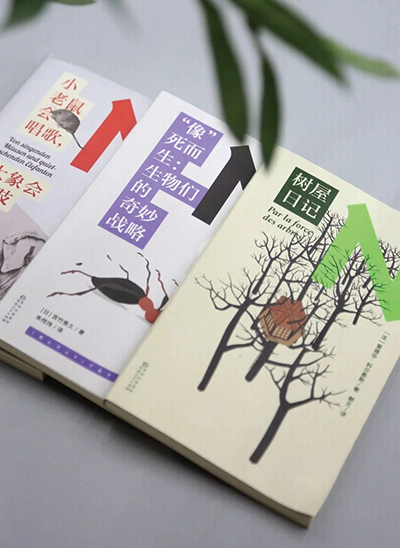
最近,曾广泛流行的口袋书、文库本又再次翻红。有行业媒体表示,在当下的图书市场变革浪潮中,一股“小而美”的潮流异军突起。文库本、口袋本正成为出版业新的增长点与热议焦点,这反映了读者阅读需求的迭代升级。
那么,翻红后的口袋书、文库本,是如何成为图书市场新风向标的呢?
口袋书、文库本的翻红很突然吗?
前一段时间,不少口袋书、文库本集中上市。如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口袋本”已推出硬汉派大师劳伦斯·布洛经典的“雅贼系列”、日系推理小说中极有个人特色的伊坂幸太郎的代表作,中信出版社的“无界文库”第一批包括《悉达多》《局外人》《老人与海》《我是猫》等20种小开本世界文学经典,还有岭南古籍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未读等出版机构不约而同地在新媒体平台以“适合假期带出门的口袋书”为切入点,推荐文库本、口袋书。而像中华书局等老牌出版机构,更是将经典古籍的口袋化包装视为一种常态,其“中华经典指掌文库”就包括《论语》《老子》《菜根谭》《纳兰词》等。
这一拨口袋书、文库本的集中亮相并非偶然,而是出版机构对变幻莫测的图书市场精准研判之后的“重拳”出击。
口袋书、文库本其实由来已久。口袋书、文库本大抵是指开本小于小32开、不超过10个印张的书。其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7月在伦敦出版的“企鹅丛书”,这套书3年间销售2500多万册,获得巨大成功。从内容维度来看,口袋书、文库本的特点是篇幅较短、信息集中、简明扼要、易读易懂、内容丰富——涵盖了人们生活学习中的方方面面。20世纪80年代,笔者买了不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五角丛书”,这套书轻薄小巧、题材丰富。2001年,笔者在日本考察时,走访了小学馆和讲谈社,在它们的社办书店里,展销着很多口袋书、文库本。后来在日本的地铁上,也发现很多乘客不是在看漫画书,就是在看文库本;地铁附近的便利店里,也随处可见文库本的身影。这让笔者意识到,文库本在日本已是深入人心的图书类型了。
口袋书、文库本该如何再造?
口袋书、文库本可以无缝融入读者的日常生活,能让他们最大化地利用碎片化时间,让阅读发生在排队、候车、购物、睡前等零散场景里。因此,当下策划推出口袋书、文库本,不能仅仅追求形式上的酷似,还要特别契合年轻读者新的阅读需求。
从一些口袋书、文库本的市场表现,我们也能窥见年轻读者的阅读品位:“新流文库”的“阅读避难所”系列,单品最高发货量近20万册;“随身轻经典”系列,年发货量25万册左右;“轻读文库”近日推出的北村薰“圆紫大师与我”系列,上市3天单册销售超6000册。
上述出版品牌都是近年来颇受读者认可的当红口袋书、文库本系列。显然,这些书聚焦的都是公版图书中适合轻量化阅读场景的品种,既能保证内容的经典性与可读性,又赋予其新面孔,给读者以新鲜感和现代感。
市场还有增量空间
笔者以为,口袋书、文库本的这股热潮不会稍纵即逝。原因是,如今的年轻读者对阅读的兴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价值,还要讲究开本、定价、选题深度、装帧风格,期望获得多重文化体验。
口袋书、文库本的内容向度未必只是轻小说,很多严肃话题都可以通过合适的包装重新焕发生机。一些历史类、政治类、哲学类选题,照样可以以口袋书、文库本的形式走红。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去年下半年陆续推出“满格·历史人文”系列第一批6种图书,上市当月即加印,累计销量已达6.4万余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悦读人大”口袋本系列,上市2个月实现加印,目前已销售上万套。
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上对口袋书、文库本的分享“笔记”也越来越多,更多人喜欢或关注到了这种图书类型。甚至有人把2025年称为图书市场的口袋书、文库本“元年”。
不过,想让口袋书、文库本受到读者和市场的持续青睐,出版机构还需深入研发、打磨产品,从内容、形式和功能3个维度发力,让口袋书、文库本既有内容品质,又能在形式上脱颖而出。
(本文编辑:周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