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学军在一次访谈时曾说:“我在创作上总是不愿意重复自己,努力追求每部作品都会有突破,有变化”,我在多次阅读这本《大鸟》的过程中,也在试图找寻她所孜孜以求的“突破”“变化”。只有一遍又一遍揣摩文本才能灵光一现地察觉,在彭学军流畅恣意的对生态文化的诗意书写之下,潜藏着一条隐秘的河流,起到了架构故事结构、推进叙事进程、建构人物形象、传递思想主题的重要作用。这条奔流在故事之外,却又给故事推波助澜的河流,就是奇幻的“梦境叙事”,它既可以理解为小说复调结构中的一层,又可以视作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虚拟镜像和参照标识。
《大鸟》中对梦境叙事多种可能性的有益探索,是理解和把握保护白鹤这一生态主题的一条“康庄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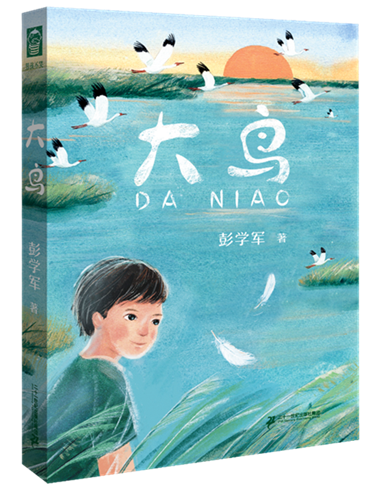
彭学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3年11月
梦境叙事将人物底层的潜意识具象化,关照现实困境和人物内心挣扎的旋涡,从而抵达挖掘人物无意识的心理动因的彼岸,实现文本与读者深层交流的能力。《大鸟》第一次谈及周蔷的梦境,是她连续两天梦到羊,从而下定决心包田种藕来为白鹤提供过冬食物,这次梦境书写一笔带过,没有细节的描写,留下悬念增强了叙事张力。在藕田里的水被人放空之后,周蔷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半夜她再次梦到了羊。这一次,作者不再三缄其口,而是和盘托出,解释了梦的源起。周蔷初一秋游期间曾经被迫放弃营救一只落入枯井的羊,这成为扎在她心底的一根刺。“羊”在文学作品中历来都是无辜弱者的隐喻,在这里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指向所有动物乃至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象征意味。而这个反复击中她内心的梦境,则成为周蔷保护白鹤、面对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原动力。周蔷的这种救赎心理,何尝不是人类曾经对大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而导致生态恶果,所寻求救赎之路的一种映射呢?
梦境叙事轻松跨越时空限制,以多时空的交叠挪移构建梦境与现实的互文性文本,让历史、现实和未来同时在场,有效地延展了故事的叙事和阐释空间。周蔷最后一次梦见羊,是在最迷茫无助的时候,她鬼使神差来到敦煌,在莫高窟的壁画中与白鹤的影像不期而遇。在随后周蔷的梦里,敦煌莫高窟中的白鹤与羊联系在一起,羊的背上驮着那只仙界的白鹤,穿过明明暗暗的洞窟后,都飞走了。这样超越了日常经验的变异性的梦境绝非是随意的讲述,而是凝练为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枯井中的这只羊经由此,与数千年历史中白鹤图腾与象征符号链接起来,影影绰绰地重叠在一起,再加之周蔷这个现实人物面临的困境,组成了一幅“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梦幻之境。无论是羊的隐喻、白鹤形象的历史纵深感,还是生态保护的现实困境,都通过梦境谱写了一曲反映生态保护者艰难跋涉之路的时代壮歌。
梦境叙事并非是对个体意识的简单复刻和临摹,而是深度再现人物精神世界与外部生存环境的正面冲突与纠缠。周蔷在藕田缺水的情况下,她和蒿子不约而同地梦见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而巧妙的是,第二天醒来藕田里竟像梦里一样一片汪洋,原来有人半夜抽水偷偷帮助他们。这样的梦,其实是周围村民沉睡的生态文明意识逐渐觉醒的一次缩影。还当停车场工程启动打破了藕田周围宁静的自然环境,蒿子梦到自己到停车场扎汽车轮胎。梦境里一个孩子气的举动,却是周蔷和几个孩子当时迷茫绝望的情绪镜像,更像是一种对于现实困境的徒劳诘问和无声反抗。
梦境叙事搭建起一个完整的“大鸟回来——归去——回来”叙事结构。《大鸟》的开头和结尾有一根神奇的羽毛,蒿子拥有这根羽毛,它带有轻盈、柔美的气质,是白鹤的图腾,是蒿子梦境之舟的压舱石,更是连接大鸟出生地雅库特、五千三百多公里迁徙路线的重要叙事装置。小说一开篇,介绍说蒿子是依据这根羽毛来预测大鸟归期的。这样的梦境叙事似乎有意识地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之间的边界,一群大鸟商议如何长途迁徙,大鸟中的王则强调羽毛上闪闪发光的日子是一个“承诺”。这种具有浓郁神秘主义色彩的梦境书写,赋予了大鸟一种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神性气质,同时梦境内外的羽毛形成一种互相映射的镜像关系。而梦境中大鸟的承诺则暗合了周蔷对羊、对白鹤的承诺,在梦境叙事中强调和重塑了动物与人类彼此的信任和依赖关系。
在梦境叙事中,蒿子与一只大鸟发生身份的交叠,化身大鸟群体的一员,这种突破人类与动物的限制,从某种意味上可以视作是人类对动物的充分认同感的体现,也必将更强有力地唤醒与催发传承多年的生态记忆和保护生态的历史责任。来自白鹤出生地的雅库特夫妇赠送蒿子一个白鹤挂件,蒿子则回赠了他所珍视的那根神奇羽毛。这种友好互赠的形式,在隐喻层面实现了关心、保护白鹤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传递、延伸、发酵和共鸣。到了故事结尾,大鸟归来之后,一根差不多的羽毛飘飘忽忽落在了蒿子的手上,在这一刻梦境、想象与现实汇聚在一起,整篇小说由一根羽毛开始,又由一根羽毛结束,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就如同经历了一番波折的几个孩子已悄然成长,鄱阳湖畔的老百姓也更加认同和融入生态保护、白鹤保护的生活。
在对《大鸟》的梦境叙事进行复盘之后,我们惊喜地发现,当生态文学创作之中融入了浓烈的梦境叙事因子,角色的心理刻画有了更为深入可感的参照物,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有了更为宏阔的背景与纵深,而生态保护的主题也可以在梦境叙事中有了更为丰富的隐喻符号和想象空间。可以说,《大鸟》充分展示了作家对生态文学书写的更多可能性的实验和探索,也呈现出彭学军式的关于爱与温情、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等内容创作的优秀范例。
*本文作者周长超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本文编辑:余若歆)